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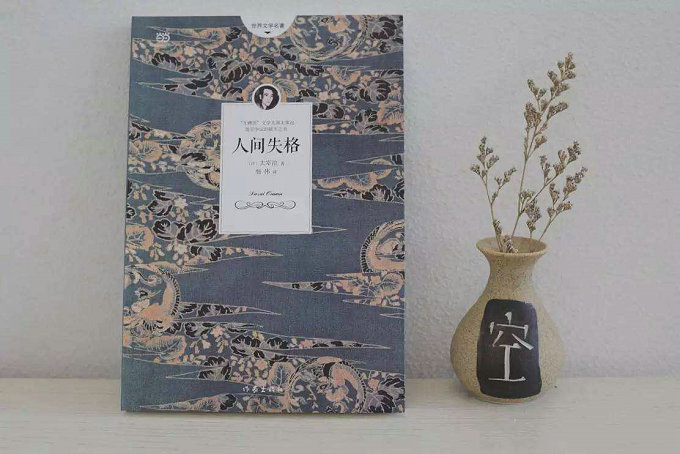
《人间失格》,日本战后”无赖派”文学的代表作,出自太宰治之手。小说以作者的自白为线索,通过叶藏的三封手札,诠释了太宰治对人类社会及人生意义的思考。
作为一部半自传性质的作品,《人间失格》深刻反映了太宰治自身经历与精神世界的矛盾。小说的”前言”和”后记”中”我”的视角代表着作者本人,而手札中的”我”则指代主人公叶藏。这种双重叙事的手法揭示了太宰治自我的复杂性,同时也体现了《人间失格》独特的”私小说”风格。
在序言中,太宰治通过描述叶藏的童年、青年和壮年的照片,对自己的生命历程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否定。叶藏自认为”丧失了做人的资格”,这不仅反映了他与人类世界的格格不入,更揭示了他对周遭社会与人性的失望。

叶藏的自我放逐体现在他对自身感受的压抑,以及他对人际关系的恐惧。他形容人类就像草地上安逸的牛,会突然甩尾,将身上的牛虻打死。叶藏惧怕暴露自己的真实情感,生怕给自己带来伤害。这种脆弱与敏感,成为了他无法融入社会的障碍。
叶藏的痛苦不仅是个人境遇造成的,更是他对人类社会本质的深刻省思。他无法接受世界的虚伪与冷漠,更无法苟同人们为迎合他人而放弃自我的行为。叶藏的”小丑精神”反映了他对现代人缺乏真实和自我认知的批判,也揭露了人类社会病态的本质。
尽管叶藏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,但小说的结尾却通过酒吧老板娘之口,以”神一样的好孩子”来评价这个”人间失格”的人。这表明太宰治本人是一位有着极高理想与追求的理想主义者。他渴望自我实现,却深陷于社会现实与内心世界的矛盾之中,最终以悲剧收场。
《人间失格》的意义不局限于太宰治个人的抒情,更在于它揭示了人类普遍存在的”生而为人的困惑”。叶藏的经历和思考深深共鸣于每一位孤独的个体。在追求群体接纳的过程中,人们往往会迷失自我,陷入彷徨与矛盾之中。小说以叶藏的悲剧,警醒人们正视现实的残酷与自身的渺小,并呼吁人们不断探索自我,找到真正的归属。

值得注意的一个微妙细节是,叶藏从小就没有饥饿感。全家的三餐时间,成为他记忆中最痛苦的时刻。这种生理上的差异,导致叶藏在心理上与人类产生了疏离感。这种疏离感演变成了自卑感,让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为异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种感觉被不断放大。在第二部手札中,叶藏自述:
有一个词语叫“湮没于世”,似乎是用来形容世间的可怜虫、失败者或无良人士的。但我认为,我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湮没于世,因此每次遇到被人指责的同类,我必然温柔相待。我那温柔的心房,连我自己都如醉如痴。
在一些译本中,“湮没于世”这个词语被翻译为“边缘人”。在自我放逐之后,叶藏表示只有在与妓女呆在一起时,他才会感到安心。因为他认为妓女是自己的同类,他们都是“湮没于世”的边缘人,甚至都是“人间失格”的人。

在《人间失格》中,太宰治不止一次借叶藏之口提到“世人”这个概念。当堀木说“世人不会饶恕你”这句话时,叶藏心想:
所谓的世人,不就是你吗?
所谓的世人,不就是你,就是我,就是每个个体吗?当我们担心某种行为会被世人如何看待时,不就代表了我们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吗?
所谓的世人,虽然是由每个个体组成,但当这些个体形成“人群”后,就会变成群体,变成大多数。大多数人很多时候是不讲道理的。这又回到了我在前文中提到的,那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,即关于人的定义。
所谓丧失做人的资格,那么相对来说,怎样才算符合做人的资格呢?换句话说,人应该什么样?我认为如果不精确定义,可以简单回答为“大多数的样子”。如果你过于与众不同,那么你很可能“人间失格”了。然而真是这样吗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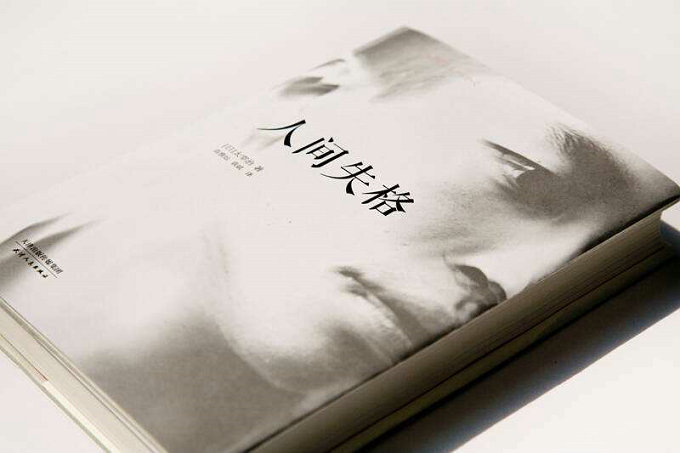
有一个故事,说一个人流落到盛产致幻蘑菇的荒岛,岛上居民因吃了蘑菇而变成了疯子。但在他们眼中,自己是正常人,而这个刚到岛上的人才是疯子。于是为了生存,尽快适应岛上的生活,这个人最终选择痛苦地吞下蘑菇,变成和岛上“大多数”一样的“正常人”。
就像在阅读《人间失格》时,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部绝望的小说,感觉很“丧”,于是少数人便先入为主地随声附和。但我却不这么看,虽然读了两遍,也感觉得很“丧”、很绝望,然而在读第三遍时,我在这种绝望中看到的却是更多的抗争,甚至希望。
叶藏是一个坚决抵制少数派的人物,他的这种精神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抗争和希望。虽然小说的结局是悲剧,表明了个人力量的渺小。但太宰治也告诫世人,应该避免过于偏激、过于追求完美而走上绝路。这是我在小说消极表象背后,所看到的积极内涵,如他在写作《二十世纪旗手》后面所说:
我在万分绝望之中,写下了《二十世纪旗手》;但我依然深信,在绝望的彼端,一定充满了希望。

群体虽然不代表正确,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融入群体都代表妥协;更不是所有的妥协都叫“同流合污”,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个词,就是“出淤泥而不染”。
所谓的世人,就是由千千万万个个体组成的群体,群体的性质由个体决定,当个体不甘堕落时,群体就有希望。